我自幼即在父亲膝下,直至他去世从未离开过。父亲一生谦虚,很少和家人谈及他早年的事蹟,也从未见他向学生夸耀过自己,因此对他早年的经歷知者甚少。晚年的情况由於是我亲眼所见,故至今记忆犹新。
父亲一生酷爱拳术,钻研拳术。他曾对我说,行、动、坐、卧无一不是在练拳,拳之理存乎於万物之中。他本人的日常功课便是练拳、写字、读书。我常常见他忽而习字、忽而又练上一段拳,方才收住手脚,立刻又拿起书本,时常脸上露出似有所悟的神情,便记在一个笔记本上。这是一个厚厚的本子,上面记满了他的心得体会,可惜后来此本落入他人之手,至今下落不明。
他教我们练拳极为严格,要求练拳时精神集中不容鬆懈。有时我们两三遍还学不会,他就感慨地说:「我当初学拳,老师只教一遍,哪像你们,有我手把手地地教还不会。」记得在学八卦剑时,我和父亲练对剑,他常用竹剑把我的手腕点得青一块紫一块,母亲心疼地责备起来,父亲说:「不如此她永远记不住。」令我继续练下去。
父亲虽然武艺大成,但仍不放鬆基本功的锻鍊。记得在我家的裡外屋之间掛著一个布门帘,父亲每经过时都要抬腿踢上几脚,而每次又是足尖点在同一个部位,久而久之那裡就破了,母亲只好补上一块,过一段时间又破了,就再补一块,不知补了多少次。
有一次我和父亲在屋裡推手,数合之后我只觉得突然两脚离地急速地向著后面飘去。时值冬天,后面正是一个火炉子,我下意识地想著「完了」,坐在一旁的母亲也惊呼起来,可是声音未落,父亲已经把我拉住又轻轻地放回原处。在此后的几十年中,我还未曾见过推手有达到这样境地的。
父亲自幼家贫失学,他的文化全是习武之餘刻苦自学求得的,他精通诗书,特别是易经,谈论起来常使文人学士为之折服。父亲的弟子中颇不乏文人,有许多就是看到父亲著作之后至我家访问,倾谈之后磕头拜师的。过后有不少人告诉我说,当初以为一个武人能谈出多少道理?及至交谈之后才觉得老师学识渊博。那时,家中几乎每日都有人来访,不少是来比武的,父亲总是茶饭招待之后再与之比较,大多是拜师之后离去的。父亲常对我说,要以德服人,以理服人,不要以力服人,这样才能使人心服口服。
父亲七十岁时任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,我也随之同往。记得开学典礼上,同学们请父亲表演一下,父亲笑答道:「好,就在这大厅之中,你们一起来捉我,有摸到我衣服的就算他优胜。」话音刚落,一百多学生一拥而上,父亲长杉也不脱去,在这个能容纳四五百人听讲的大厅裡,或从人隙中,或从头顶上,往来飘忽。我站在旁边也未能看清楚他究竟是如何闪转腾娜的。好久,眾人都气喘吁吁,也未能有人摸得一下。
在镇江的时候父亲经常带著我们出外散步。一日晚饭前,父亲又带著我们一群人出外散步。国术馆建在镇江阳彭山上,出门便是山路,父亲指著上山路说,你们练了这麼久,不知功夫可有什麼长进,你们愿意试试吗?我们都表示「愿意」。父亲说:「我在前面走,你们在后面追,有追上者为胜。」说完向山上走去,我们在后面使出全身之力紧追不放,追了有二里多路,父亲始终将我们落下丈餘,看我们实在跑不动了,父亲方收住脚步,哈哈一笑说,你们的功夫还差得很远,还要多努力才是。他对我们说,年轻时从郭云深先生学习时,经常是郭先生纵马驰骋,而他自己则手揽马尾日行百餘里。父亲年轻时确实极有脚力,他从保定步行至北京,总是夜间啟程天明即到。
对於练拳,父亲一生有不少体会,但他经常说拳术的诀窍就在一个「练」字,「人一能之己百之,人十能之己千之」。他自己会拳械百餘种,内功更是超凡,但每到一处,总要寻访高人逸士,讲求技艺。他经常教导我们说,艺不压身,要虚心向别人学习,博採眾家之长,如海之纳百川。
父亲一生从无门户之见,无论内、外家拳师,只要来访一律热情招待。对於当时武术界出现的个别恃强凌弱甚至欺师压人等现象,父亲非常气愤,嘱我们切不可学,一生要谨守「忠厚」二字。
这些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,现在的时代和那时也不大相同了,但许多道理对今日的后学者仍可借鉴。上述如果能对大家有点益处,那就是对先父最好的纪念了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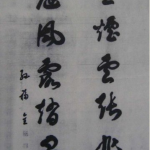



孙先生真乃一完人,给人以激励